论十七世纪江南地理环境与文化世族
- 体育资讯
- 2024-12-27 04:57:59
- 19
作者简介
姚蓉,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上海市“浦江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三级教授。现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常务副主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研究诗词学与明清文学。主持在研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词坛唱和研究”(10CZW031)等科研项目11项,在《文学遗产》《南开学报》《中国语文》等海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明末云间三子研究》《明清词派史论》等学术著作9部,科研成果《郭麐诗集》获“全国图书古籍整理奖”二等奖,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摘 要
十七世纪的江南,按照明清时人的观念,主要范围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其总体地域特征是多“水”,具有地多膏壤、农桑之业甚裕,水网纵横、商贾之业发达,湖山嘉丽、自然环境优越的特点。江南之民仁柔,历来不乏退隐避世的传统,但是随着明末政治腐败的加剧,江南人也显示出倔强、血性的一面,具有“兼济天下”的勇气和行动力。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极度繁荣,世风奢华,但经过战火的摧残,繁华、富庶的江南迅速凋敝。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分为官宦型文化世族和才艺型文化世族,不少世族是二者相结合的类型。文化世族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是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苏州府以科举取胜,松江府以文学取胜,常州府以学术取胜。其时文化世族的兴盛,是地理环境、地域文化与居于其中的世族相互促进、互惠共赢的结果。
关键词
十七世纪;江南;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世族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此论虽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学术变迁而言,但“家族复限于地域”一语,却是适用于历史上所有族群,包括文化世族。曾大兴先生因此指出“考察家族的地域性,则应使用地理的方法”。故此,在走近江南文化世族之前,需先了解十七世纪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一、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
江南只是人们对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惯常称呼,要确定它的具体范围,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时至今日,江南的地域范围仍未有统一的界定。
1
何处是江南
要划定十七世纪江南的地域范围,当时人的“江南观”应该最有参考价值。生活于明清之交的宋徵舆(1618—1667)在崇祯十六年(1643)专作《江南风俗志》一文,其中是这样定义“江南”的:南直五郡: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浙江三郡:杭州、嘉兴、湖州,江南具是矣。宋徵舆对“江南”的界定是非常明确的,即当时南直隶所辖的应天(入清改为江宁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及浙江布政使司所辖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入清后,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宋徵舆提到的这五府均在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康熙元年(1662)改浙江布政使司为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仍为之所辖,俗称浙西。
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四《水学》中提到“江南”时,有云:
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
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在其观念中,以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及太仓直隶州为江南核心区域。
当今学者在研究江南时,也多沿用明清时人的界定,如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所指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李伯重先生将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界定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
本文在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的社会与文学时,亦参考上述研究,按照宋徵舆的分法,将“江南”范围划定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由于太仓州从苏州府析出是在雍正二年(1724),故本文仍将它视为苏州府的一部分。这八府所在的区域,又被称为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李伯重先生认为,这一区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虽然李伯重先生对江南地区的界定是从经济角度入手的,而就文化区域而言,环太湖流域的这八府无疑也是一个整体,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它们有的属于浙江,有的地处江苏。江苏省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地跨江南和江北,但就文化特性而言,长江以南的苏、松、常、镇等府,其物产、语言、风俗、服饰等,都与浙西钱塘江一带相似,而长江以北至徐州一带,因地近山东而更接近齐鲁文化。由此可见,苏南和苏北并非同一文化区。同样的,不论地形、地势还是经济发展、社会风俗,两浙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明人王士性指出“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吝椎鲁,尚古淳风”的人文差别,可见浙西奢华、儒雅之俗更接近吴地流风,应属同一文化区域。当然,江南文化区的范围或许还可伸展至皖南,甚至江北的扬州等府,但将其腹心地带定为太湖流域的这八府,大致不差。至于这些州府所辖具体地界,则以十七世纪的行政区划为准,见表1。
表1
2
江南之地貌
江南八府所在地域的总体特征是多“水”。其地“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除西面外,三面环水。这片地域还拥有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湖泊面积为2427.8平方公里,横跨江、浙两省,东近苏州,南濒湖州,西依宜兴,北临无锡。太湖水古经吴淞江、东江、娄江等三江,分别向东、南、北三面排水入江入海。此外,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经过这片地域的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等处。再加上八府之内遍布各地的小河道,确实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江、河、湖、海各种水资源的江南水乡。
江南八府,或濒海,或临湖,或沿江,都与水密切相关。宋徵舆的《江南风俗志》载:应天府“濒江数百里”,“江水足溉灌”;苏州府“其地绾八省,舟车辐凑”;松江府“其地濒海”;常州府“土厚水深”;镇江府“自吴越水行浮江而北者皆汇焉”;杭州府“其地依山湖,负江海”;嘉兴府“其地多溪泽,少林莾”;湖州府“其地多溪山,山五溪十”。在水的滋养之下,江南八府有以下地理特征。
第一,地多膏壤,农桑之业甚裕。如应天府之民“屯种以时,斯农桑衣食之业甚裕”;松江府之民“专仰耕作,土宜稻麦术绵,妇人善织,其布亦他郡所仰也”;嘉兴府“有陂池蒲鱼之利,土宜稻麦术绵,称为膏壤”;湖州府“土宜蚕桑,妇女无贵贱,皆善治蚕,隙地遍桑,是以丝缟冠天下”,“平原则膏壤”。江南八府所在的环太湖流域,六分之四的面积是平原,水资源丰富,适宜种水稻、桑等农作物。研究太湖流域经济史的学者指出:“明代以来,太湖南岸湖地的农桑经济体系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正是这一内在的自发性,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在明代中后期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时候,能够平稳过渡,安全着陆,并且在清代至民国的三百年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环太湖流域的农桑经济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的主要特征,是江南社会繁荣和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事实上,明代嘉靖、万历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水平就已远远高出其他地区,在明末各州府的粮额数中,全国总计28270343石,其中南直隶7413165石,占总数的26%,北直隶为587948石,仅为南直隶的8%。至清代,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之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另外,苏、嘉、湖等府自两宋以来,桑蚕业就十分发达,明清时期更是丝绸业兴盛地区。如湖州归安之菱湖镇“多出蚕丝,贸者倍他处”,嘉兴梅里镇“民务农桑,所织绸最著名”,苏州府震泽县“邑多栽桑以畜蚕”,等等。直到今天,苏州、嘉兴和湖州等地出产的丝绸仍然享有盛名。
明代江南区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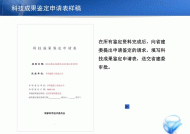












有话要说...